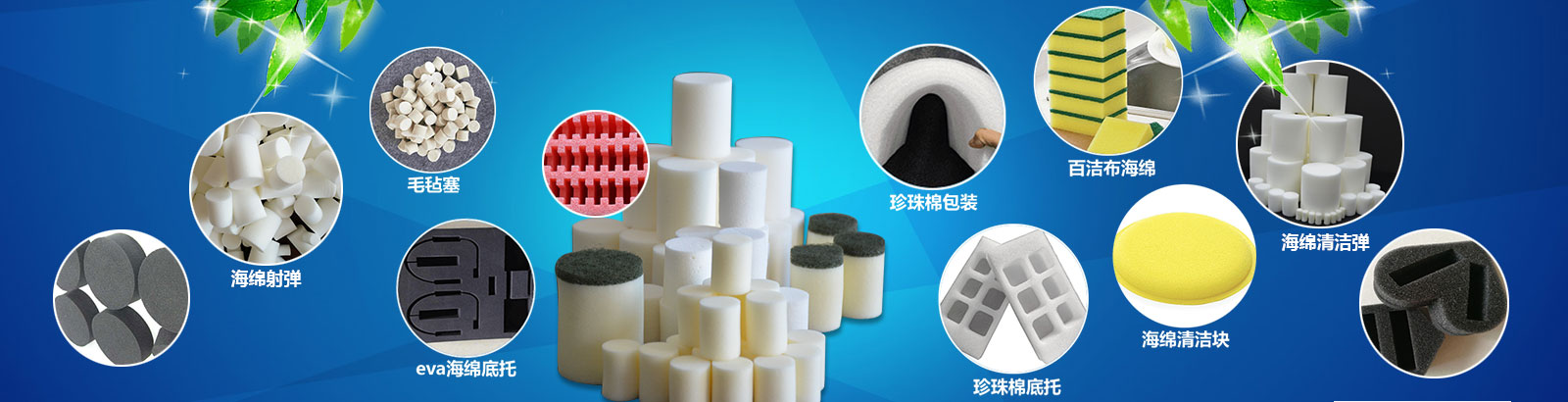老舍言语的魅力
20世纪90年代,我曾安排过一次“文学言语标准化”评论,引起文学评论家和言语学家很风趣的争辩。一位闻名文学评论家说:“文学言语本质上是反标准的”,文学言语寻求的方针便是“扭断语法的脖子”。此话一出,当即遭到言语学家的剧烈辩驳:这话并没有“扭断语法的脖子”,要想“扭断语法的脖子”,就得“把这句话说成‘脖子的语法扭断’或‘的扭断脖子语法’”。他的意思是,把话说得不成人话,完全背离汉语语法,才算“扭断了语法的脖子”。

那么,文学言语与言语文字标准是啥联系?我们说,宜发起文学言语遵从汉语的一般标准。例如,在文学言语中削减病句,尽量不使用不合当时标准的词形(如不把“凭仗”义的“借”写成“藉”,不把“执着”写成“固执”),正确运用复句中的相关词语,力避标点符号过失,等等。走上屏幕的文学言语须尽量不读错字音。文学言语的标准化,并不阻碍作家言语的个性化与发明性,而是使得文学言语更顺利、更熨帖、更好懂,成为引领社会的言语模范。威望词典的许多示例来自文学名著。
老舍是注重言语标准的作家。1955年,老舍在《北京日报》属文,对推行一般话表明火热支持,“期望北京市的话剧艺人和歌剧艺人都负起这个政治任务,下功夫把握北京语音,在推行一般话上起示范作用,扩大影响”。他还在《人民日报》上说,文学家对遍及民族共同语负有责任,“意大利的但丁、英国的乔叟和我们的曹雪芹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功劳”。1956年,老舍被任命为中心推行一般话作业委员会副主任。
20世纪50年代,老舍对自己的文学言语进行了显着的调整。胡宗温等北京人艺的老艺人告诉我一件事:1951年扮演的《龙须沟》中,有个词儿叫“日崩”,外地观众反映听不理解这个北京土话,老舍后来发明话剧《茶馆》时,就再没用这类土词土语了。
我找来《龙须沟》剧本细阅,果然发现了“日崩”这个词:(1)这家伙,照现在这样,他蹬上车,日崩西直门了,日崩南苑了,他满天飞,我上哪儿找他去?这句台词里的“日崩”,是个地道的老北京土词儿,用来“描述走得忽然,爽性利落,无所顾念”,也便是表明“一会儿跑到哪儿去了”。“日崩”在北京话里的读音是rībēnɡ,跟一般话读音不大相同,外地观众听了,连是哪个字都弄不清,天然听不理解。
《龙须沟》中,北京土词不少。例如,(2)谁也没想到这么早就能下瓢泼瓦灌的暴雨。(3)您看,这双鞋还线)滑溜溜的又省番笕又省碱。(5)巡长我说今儿个又得坐蜡不是?(6)今儿个他打连台不回来,明儿个喝醉了,爽性不好好干啦。这几句线)中的“瓢泼瓦灌”描述雨势凶狠。(3)中的“抱脚儿”指鞋袜尺度适宜。(4)中的“番笕”指香皂或番笕。(5)中的“坐蜡”指堕入尴尬地步,或许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。(6)中“打连台”的“连台”是“连台本戏”的简称。“连台本戏”也叫“连台戏”,指连日扮演的大戏,这个戏由多个戏本构成,每天只扮演一两本。“打连台”是说戏班子唱连台本戏,天天唱,要唱若干天,常用来比方做事情中心不歇息,接连做,继续多日。这些话现在简直绝迹了。
不少北京的土词土语,有很多说道,外地观众乍一听,天然难解其意,因此影响了扮演作用。这种状况传到老舍耳中,他觉察出其间弊端,在一篇文章中说:“我曾经爱用土语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某些土语的表现力强啊。但是,经历把我的道理碰回来了。表现力强吗?人家不理解!不理解可还有什么表现力可言呢?”基于此,老舍对自己著作的言语进行了调整。他举例说:“假若‘油条’比‘油炸鬼’更一般一些,我就用‘油条’。相同的,假若‘墙角’比‘旮旯儿’更一般一些,我就用‘墙角’。”这种变更在1956年扮演的《茶馆》中表现得非常显着,《龙须沟》中呈现的那些土字眼儿,一个也找不着了。但是,有两样东西一点儿也没削减。
一是京味儿。《茶馆》第一幕可谓经典中的经典。随意找两句话,一听,便是老北京话——精练,幽默,脆生生的。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两句“京腔”:(7)常四爷:要抖威风,跟洋人干去,洋人凶猛!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,尊家吃着官饷,可没见您去冲击交兵!(8)二德子(四下环视,看到马五爷)喝,马五爷,你在这儿哪?我可眼拙,没看见您!这些话说得太地道了!《茶馆》里这些胡同俚语的精妙绝伦之处,就在于没用一个北京土词儿。这便是老舍的“神功夫”!
著名艺人于是之曾扮演《茶馆》中的核心人物,裕泰茶馆的掌柜王利发。他在《老舍先生注重文学言语的标准化》一文中写道:“在《茶馆》中,能够说一个让外地观众(或读者)隐晦的土词都没有,但《茶馆》的北京味儿仍然像《龙须沟》相同稠密,没有一点点削弱。”
老舍的京味儿最典型、最精彩地表现在人物对话上。《骆驼祥子》里买祥子骆驼的那位老者的几句话,让人激烈地感遭到浓郁浑厚的京腔京韵:(9)“这么着吧,店员,我给三十五块钱吧;我要说这不是个廉价,我是小狗子;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,也是个小狗子!我六十多了;哼,还教我说什么好呢!”能够说,老舍不是凭着肚子里沉淀的古都土词土语来表现京味儿的,而是经过京城子民言语的韵致、派头、习气说法以及人物的思想办法、脾气品性来展现京味儿的。所以,老舍能做到不用一个佶屈聱牙的土词,就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京畿声调的神韵。
二是艺术性。放弃土词土语了,但《茶馆》的艺术性一点点没削弱。看过《茶馆》的人无不赏识其间的妙语。如王利发说:“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?我开罪了谁?谁?皇上,娘娘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,单不许我吃窝窝头,谁出的主见?”再如常四爷说:“我爱我们的国呀,但是谁爱我呢?”这些话栩栩如生地描写出了人物的性情、内心世界和人生感触。
老舍曾说,他能用《千字文》里的字来写著作。《千字文》是古来儿童发蒙的教科书,相当于识字讲义,里头大约有一千个字。汉字的常用字有三千,一千字显然是最基本、最常用的字。用这样的“根底用字”来写东西,显着是冲着一般大众去的,他想让里巷庶民一读就懂、一听就理解。
老舍先生用最一般的文字,给我国文坛奉献出全世界冷艳的文学艺术之花。他说:“像‘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’,像‘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’这类的诗句,里边都是些极一般的字,而一经诗人的加工发明,就成了永存的名句。”
自古以来,用一般、好懂的词语写出的东西易于撒播。李白的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跟说话相同,传诵千古。让大众好懂,不仅是老舍写作的夙愿,并且是他对文学艺术的热忱希冀。老舍曾提议变革京剧中的念白。他曾说:“我主张:京剧艺人的道白能够不能够更天然一些,不用把字音迁延得很长?京剧艺人都能讲很好的京腔调一般话,若是把道白放天然一些,挨近白话的腔调,或许关于传达京音的一般话不无影响。还有:‘上口’的字能够不能够改用京音来唱?在三四十年前,艺人把尖团字念错了,台下就会有人给叫‘倒好’。现在,艺人们已不严格地考究区分尖团,台下也不那么挑剔了,那么何不爽性也撤销‘上口’的字呢。”
老舍说的京剧中的“上口字”指跟一般话中读音不同的字。他说的“艺人们已不严格地考究区分尖团,台下也不那么挑剔了”中的“尖团”,是指尖音和团音。“团音”是指一般话中j、q、x跟i、ü或i、ü打头儿的韵母相拼的音节,如“记”“渠”“卷”等字的读音,便是团音。“尖音”则是z、c、s跟i、ü或i、ü打头儿的韵母相拼的音节,一般话里没有尖音。侯宝林有个相声,叫《关公战秦琼》,扮演时,侯宝林说了句京剧道白:“来将通名。”其间“将”的发音是ziànɡ,这便是尖音,一般话读jiànɡ。老舍说的“那么何不爽性也撤销‘上口’的字呢”,是主张撤销跟一般话发音不同的尖音字。他的想头是,让各地观众更易于听懂京剧、赏识京剧。老舍的这个主张是从“文学艺术著作要让大众好懂、便于赏识”这个意念动身提出的。他的这个理念,当下仍值得发起和发扬。
“用大众的话跟大众说话”最有用,不论是文学著作仍是其他什么文本,无不如此。